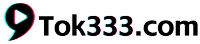责任编辑: laman-map.com
若是谈起建筑,刘晓都似乎可以绵绵不绝地讲下去。
从早年在清华和海外的求学经历;到勒•柯布西耶、雷姆•库哈斯的建筑语言以及战略眼光;再到过去的近30年间,他和建筑事务所的合伙人在深圳所亲历的城市奇迹和地产沉浮……在刘晓都的言谈里不难感受到,建筑不仅是串联他过往人生的事业主题,也在塑造着他评判事物、理解世界和看待命运的价值体系。
而在建筑领域的履历,又促成了他当下角色的独特性。五年前,经过9个多月的公开遴选,作为建筑师的刘晓都以“跨界”身份出任了深圳坪山美术馆的馆长一职。如今,他已经在这个岗位上走过了接近两届任期。
坪山地处深圳的东北边缘,距离市中心需要一小时以上的车程,是一个以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产业为特色的工业新城。以这样的基本面去发展一个立足现当代艺术的区级美术馆,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也因为如此,在外界眼中,无论是这家艺术机构还是主持运营它的负责人,自创办之初就一直带着鲜明的实验气质。
回顾五年多的馆长生涯,刘晓都表示,如今他仍然不能算是艺术的“圈内人”。面对一个建筑,他立刻就能做出判断:建筑的风格是什么,水准高不高,并且会“满眼都是细节”、“满眼都是毛病”。但是对于艺术,他“需要梳理和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然而,以局外人的视角不断与艺术发生碰撞,不仅塑造了一家艺术机构在边缘生长的样本,也促成了一次“格物”与“致知”的独特个人经历。
刘晓都说,建筑师的从业背景让他相信专业主义。在馆长的任期里,他和团队也一直在竭力以专业主义塑造着坪山美术馆的知识生产和精神资源。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得以前所未有地接触到了众多的艺术工作者,走近了他们真实的创作生活。
在刘晓都看来,在这些艺术家所组成的群像中,有一种冷暖自知的“生命感”,这种由艺术生发出来的经验,幽微而带着异彩,映照着众生喧哗的世界中那些看似严丝合缝的方法论和价值观。
而这种认知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刘晓都自己,包括他如何确认一家艺术机构的使命和职责,如何理解在地艺术生态的存在理由与信念来源。与此同时,艺术也让他有了更多的视角,可以去重新观看已经扎根奋斗多年的深圳;以及作为建筑师,他曾经的那些笃信和困惑。
 深圳坪山美术馆外景
深圳坪山美术馆外景 以下自述根据访谈整理,发布前经受访者审校。
1.跨界
“跨界做美术馆馆长,最初也是希望能受到艺术启发,回应在建筑领域遇到的困惑”
请一位建筑师背景的人去做美术馆的馆长,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作为建筑师,我们这代人赶上了过去20年中国发展的最好时光,能有机会完成大量的作品。 但其实我也会慢慢感觉到自己在创造力方面的瓶颈: 有时候想法很好,但是具体做起来,涉及到造型、空间的部分总会陷入反复,设计和十年前没有什么区别,做不出来自己满意的东西,心里也会很焦虑。
做建筑本身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建筑师所有的规划和布局,最终都要体现在每个细节里。 但在这个过程中总有无数的遗憾: 在这里改一下,那里被掣肘一下,到最后的作品就会面目全非。虽然流程一直在推进,但在每一个环节,品质都会“降个级”,等到完成以后,有时甚至都没法看了。
要做得这么累,所能坚持的自己的想法又那么有限,我又不想去做那种特别市场或说网红的东西。那么心里有时就会有疑问:建筑还是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所谓的“瓶颈期”,主要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并没有对建筑失去热情,决定跨界接受美术馆馆长的职位,最初也是希望能迂回地受到艺术的启发,回应在建筑上遇到的困惑。
直到今天我看艺术,还是不会像看建筑那样能有那么清晰的眼光, 但是建筑的从业背景让我相信专业主义。 作为一个美术馆的馆长,我希望能让坪山美术馆的出品达到高水准。坪山美术馆目前的团队成员,绝大多数此前都没有艺术领域的从业经验,而且我觉得,某些所谓的相关经验,其实也是很“糟粕”的东西。五年来,我觉得我所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用接近于企业的管理模式,带动了美术馆运营效率的提升。
回想接任馆长之初,我有关美术馆的发展构想其实很简单: 一个地处边缘的艺术机构,能够如何从无到有做出有点意思的展览,甚至形成一定的行业影响力?作为馆长,需要对此理出比较清晰的目标、步骤和方法。
 2019年11月底,在群展《共时》开幕现场,瑞士艺术家罗曼.西格纳(Roman Signer)呈现了行为表演《通道》
2019年11月底,在群展《共时》开幕现场,瑞士艺术家罗曼.西格纳(Roman Signer)呈现了行为表演《通道》 2.出招
“别人不会随随便便就对我们的工作不屑一顾”
在2019年底,我邀请李振华策划了上任后的首个大型展览《共识》,在参展艺术家中,我们邀请到瑞士国宝级艺术家罗曼.西格纳(Roman Singer)来到坪山。接着在2020年4月,随着当时国内疫情状况稍有缓和,又邀请鲁明军做了一个学术性很强的展览《缪斯、愚公和指南针》。
做这两个展览的初衷,是因为我相信,坪山美术馆不应只是以一个简单的区级公立美术馆来看待自己,它应当体现出一定的国际视野和学术标准。因此,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把美术馆的调性定下来。
在这两个展览之后,我的思考和认知是, 美术馆的工作并不应只是展示别人的作品和策展方案,它同样需要输出自己的内容和观点,要具备“自我知识生产”的能力。坪山美术馆需要生产出在此之前没有过的内容,要为当代艺术的版图贡献出新的想法、方式和思路。这是“知识生产”的目的,也是一种主动意识 。
 2020年10月,跨界项目“九层塔:空间与视觉的魔术”的首个展览:“团结就是力量”现场
2020年10月,跨界项目“九层塔:空间与视觉的魔术”的首个展览:“团结就是力量”现场 展览《九层塔》最初的想法,是我和策展人崔灿灿在一次从坪山驾车返回深圳市区的路上聊出来的。这个想法在2020年10月落地,最终成为一次时间跨度达14个月,前后共邀请了9组建筑师、设计师和艺术家联合参与创作的跨界艺术展出。
今天回头看,很多人都是通过《九层塔》才知道坪山美术馆的。那次展览也算是坪山美术馆的一个“高光时刻”,它也是在回应我一直在考虑的那个问题: 坪山美术馆作为一个新馆,它该如何立足?如何被人知道?如何建立起一种独特的价值?
在《九层塔》获得影响力之后,我们没有将类似的跨界展览模式延续下去,而是转而推出了《深圳当代艺术家系列》。在任期规划中,我并不寻求让坪山美术馆这家地处南方的公立艺术机构,变得和在北京、上海的美术馆毫无区别。立足深圳,关注并推动珠三角地区的地方艺术生态,是我最终希望做成的事情。
从全国范围来看,深圳的艺术家仍然属于相对边缘的状态,如果从刚起步就去做关注“在地艺术”的展览,注定无法快速进入当代艺术话语体系,也不会立刻形成传播效应。所以,从《共识》到《九层塔》,坪山美术馆初期推出的一系列的展览,都可以看作是为推广“在地艺术”所做的铺垫。
它们就像是一种“出招”,或是某种意义上的“秀肌肉”。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聚焦地方”这件事情真正地成立。 通过一系列能形成广泛影响力的展览形式,坪山美术馆会更加有底气地去以个案梳理深圳本地当代艺术的结构和肌理;外界也会更重视我们的目标:我们所付出的努力,就是要让别人不会随随便便对我们的工作不屑一顾。
 2023年12月,群展“游牧在南方:河流、隧道、湿热、星群”开幕现场
2023年12月,群展“游牧在南方:河流、隧道、湿热、星群”开幕现场 3.南方
“每件作品背后,都有一个鲜活的生命,有的昂扬、有的焦虑、也有的很丧”
《游牧在南方》是坪山美术馆刚闭幕的展览,展览从策划开始,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整个过程就像是一次大型田野调查。
在策展人崔灿灿的建议下,我们将展览的着眼范围扩大到中国南方的九个省市,聚焦在这个区域中一个更为“边缘”的群体——那些还没有被主流艺术生态所关注的年轻艺术家们。
直到走完全部寻访的行程,无论是崔灿灿还是我都有很深的感触。在这些年轻艺术家当中,真正取得世俗意义成功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都还没有什么所谓的名气,在生活中也会面对焦虑、苦闷和茫然。
但是在交流时,这些艺术家非常真诚放松,没有太多的芥蒂。和他们的接触,也深刻地改变了我对当代艺术的很多理解:我真实地见识和感受到了更为纯粹的艺术创作。 因为这些艺术家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并不是以艺术为生,他们对于艺术的创作会抛开对艺术市场的考虑,而这种心态带给了他们更大的自由,包括诚实、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危机和处境 。
当然,这种“自由”的状态或许也是某种说辞、某种自我的安慰、是源自现实的无奈。但就是在这种无可奈何之下,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走艺术这条路,靠做别的工作维持生活,把艺术变成自己生命里的某种追求。
这种状态也是最令我钦佩的部分:他们没有为了卖画而拼命去折腾,也没有想方设法去成为一个艺术明星,去赢得画廊的追捧,逼着自己拼命画。那样就等同于进入到另一种主流的规则当中去了。 而在那种所谓的主流规则中,艺术的角色又是什么呢?
我一直觉得,抛开艺术家本人,单纯去品评他们的作品,探讨他们的风格受了谁的影响,水平是高的还是低的、技法是好的还是坏的,还是在以一个第三者的姿态去发表评判。 这也是当下艺术界的最突出的一种状态:只看东西的好坏,但并不关注人。
若是没有经历这次走访,了解到这些年轻创作者们的经历,而是直接去展览现场看他们的作品,你可能会很简单地认为那些作品有点稚嫩、或者在哪里有点“不对路”。 但是如果能意识到,在每件作品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在那些鲜活的生命中,有昂扬的、有焦虑的、也有很丧的部分,它们所构成的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就是人间的百态。这时他们艺术的好与坏,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2023年12月,群展“游牧在南方:河流、隧道、湿热、星群”开幕现场
2023年12月,群展“游牧在南方:河流、隧道、湿热、星群”开幕现场 4.边缘
当那个“主流”的动力减弱了、激情消失了,变得平和又油腻,边缘才会活跃起来
“南方”如今在世界上也是一个持续具有热度的话题,在我看来,“南方”体现的核心问题就是: 在一个生态中,当原有的“中心”开始衰退,那么该如何看待“边缘”所显现出来的机会?
有的时候, 当位于中心的那个“主流”动力减弱了、激情消失了、荡漾的东西变少了,甚至变得平和又油腻。这个时候,中心的张力才会向外释放,边缘才会活跃起来 。从某种角度看,北京的艺术生态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都像个“黑洞”,把所有的人都吸引过去了,根本出不来。而当这个“黑洞”的吸引力开始变得松散,很多人就会向南移。可能有人会去上海,有人会来到深圳,也有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很多在“中心”呆过的人,或许并不是领域中最拔尖的人才,但他们会把在“中心”的经验、感知和视野带回到地方。他们就像是特别重要的火种,利用自己的见识和积累,在地方慢慢做起来新的事情。
这样, 由于中心所释放出来的能量,让所谓的“边缘”得到了繁荣的契机。这种能量就像散播种子,当一个人遇到某个他合适的地方,那里就有可能长出一片小东西来 。所以“南方”现在还是一个开始的状态,这里的生机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而种子已经播撒下去了。
但是看待边缘,也不应一味报以浪漫化的目光。 身在边缘,最常面对的问题,就是“被忽略”和“不被重视” 。毕竟“成规模”、“成套路”的东西往往只能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中心地带才会找到适应的土壤。
对于坪山美术馆来说,我们属于“边缘的边缘”:深圳本来在中国的艺术生态版图中就是边缘地带,而坪山在深圳也算是城市文化的边缘。如何正视这个前提,挖掘出更多有意义的东西,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挑战。至于说到美术馆接下来的发展方向,我认为目前经济环境很不好,艺术和文化也随着跌入低谷。眼下艺术最重要的命题,还是如何存活下去。
 2021年8月,“深圳当代艺术家系列之一”:迢迢--薛峰个展现场
2021年8月,“深圳当代艺术家系列之一”:迢迢--薛峰个展现场 5.深圳
“文化是能产生黏连感的东西,可以让人们对于自己身在的城市产生认同、归属和舒适感”
深圳给很多人的印象,是一个与“务实”和“发展”高度绑定的城市。
如今我在深圳已经工作生活了20多年,算是一个老深圳了。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角色,你或许会说,深圳完全可以专注于去做类似硅谷那样的地方,因而不必重视艺术和文化生态的塑造。但我也认为,如果一个城市是以发展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大都会为目标,就必须有软实力作为必要的匹配。
你现在去问很多身在深圳的人,问他们是哪里人?很少有人会说“我是深圳人”,反而可能会说“我是湖北人”、“我是东北人”、“我是湖南来的”,等等,不少人在潜意识里其实并没有把深圳当成他的故乡。
而文化是能够产生“黏连”的东西,能够让人们在彼此间产生更多的关联,进而对于自己身在的这个城市产生认同感、归属感和舒适感。城市也会因此更有韧性 。而不会说,人们想的是在这里挣了钱,再回老家盖房子去。
现在深圳已经可以算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城市了,我认为这是近十年来才发生的变化。我也期待深圳在艺术生态上能发展的更好,但这首先需要人才的汇聚。
也许深圳不会发展成为北京和上海那样的艺术中心,但是它一定会是南方艺术生态的重要节点。广东的亚文化非常发达,相比之下深圳像是一个异类:一个由北方人聚集、建设的南方城市。
也因为如此, 深圳很需要文化上的认同感。在这里生活工作的人,需要有可以共同相信和分享的东西,可以找到安放情感的地方,否则就会是一团散沙。这种“认同感”一定是依靠文化才能实现的,而不是仅仅靠经济来实现的,否则结果就是,在这里赚完了钱,人就走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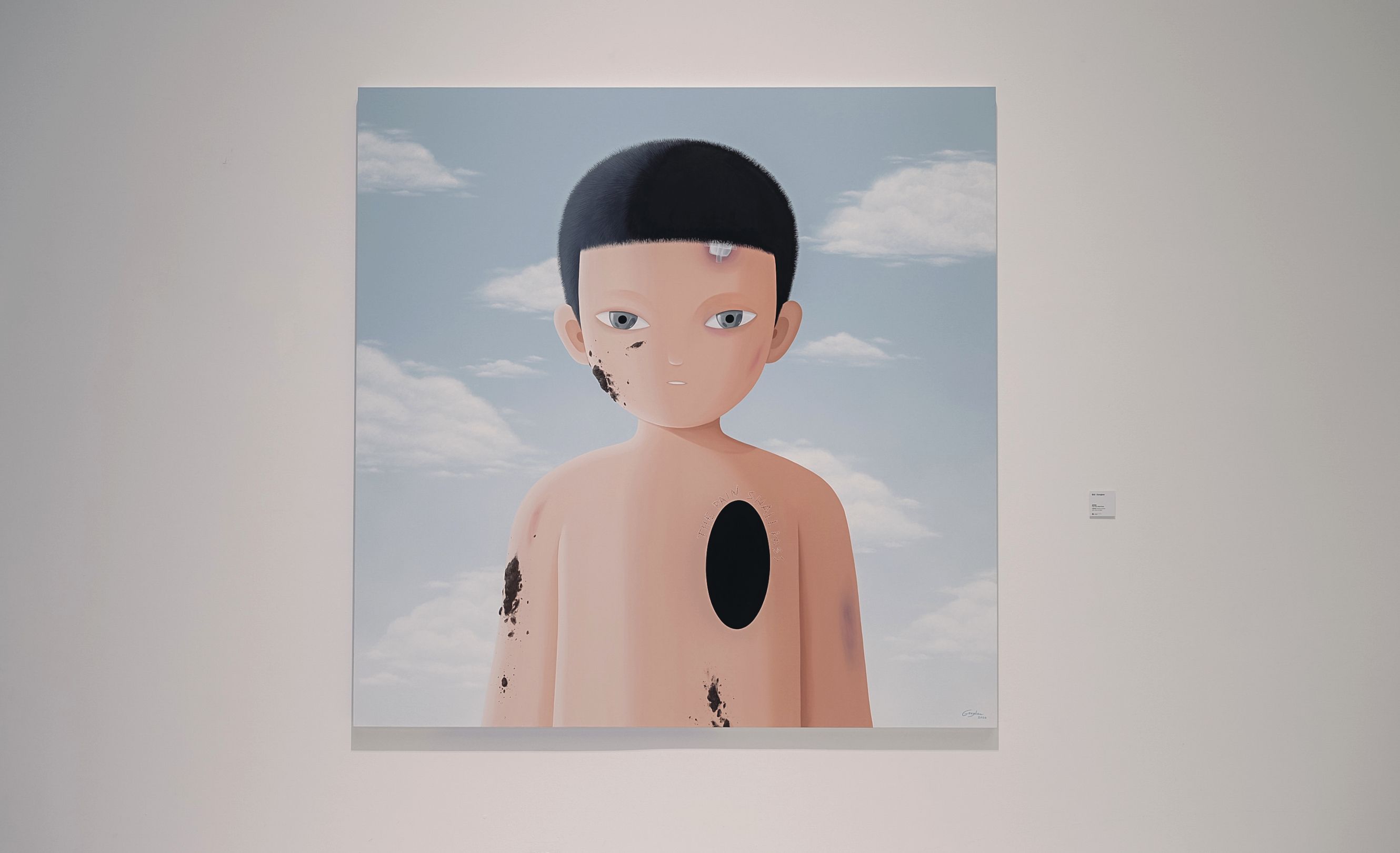 2024年7月,个展“贡坎:空心之间”展览现场
2024年7月,个展“贡坎:空心之间”展览现场 6.再谈一下跨界
建筑与艺术,“有用的”与“没用的”
我今年63岁了,不会在美术馆的岗位上工作太长时间。今天,我还会继续做一些和建筑有关的项目,但是我已经能够逐渐跳出建筑师的思维。
我会发现,建筑师其实也会有很多认知方面的局限性。建筑师们有自己的圈子、自己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会有大家公认的高峰。但是现在我也不觉得那个高峰,是要唯一追求的目标了。
在我看来, 艺术与建筑最大的区别,在于艺术是一种更为源发于个人主观的创作形式,而建筑设计是基于客观需求、为别人提供解决方案,创造力只是设计工作中的一个部分。艺术作品在被创造出来时候,很可能并没有明确的用处,而建筑设计的初衷就需要它必须是“有用”的。这个差别决定了两者在工作的态度、方法和自由度等方面是完全不同的。
建筑师和艺术家也会面对相似的问题: 是否要去与市场、资本和权力合谋,以达成自己的作品和梦想。 但相比之下,艺术家自己是更具有主体性的创作者 。对于自己的创作,艺术家可以选择拿去交易,进入市场的竞逐轨道;也可以选择和市场、和资本保持距离。这些选择在本质上都不会决定一个艺术作品的好与坏。好的艺术与好价格之间可能会有重合,但彼此不是必然关系。
 2021年11月,“九层塔:空间与视觉的魔术”的第九个项目--“论坛与回顾”,刘晓都在这次“九层塔”系列的收官项目中负责空间呈现
2021年11月,“九层塔:空间与视觉的魔术”的第九个项目--“论坛与回顾”,刘晓都在这次“九层塔”系列的收官项目中负责空间呈现 现在很多人还是会以“有没有用”的眼光去评判艺术的价值,但追溯这个逻辑的根源,还是要找到最初的那个“目的”是什么。
今天在我看来,所有以挣钱为目的的事,说到底还都是在为了维持皮囊和欲望而不得不去做的奔忙。而现代社会会把这类奔忙正当化、神圣化。但是为什么仍然还会有人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在那些“无用之用”上面?一定还是因为那里面存在一些更纯粹的、更精神性的价值。
我们人类对于创造力的关注,以及我们对于未知世界和自己内心世界的种种思考和表达,其实都是在回应“如何度过这一生”这个命题。从这个角度看,艺术的人生,是很值得过的一种人生。
文章编辑: laman-ma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