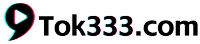责任编辑: dolighan.com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博物馆已经成为人们交流、朝圣、反思、慰藉的场所,甚至可以说是精神滋养的场所。这一点在最近的新冠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出于恐惧,大批民众前往博物馆参观,思考艺术作为远离疫情的解药,更不用说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恐怖所引发的政治动荡了。”
曾担任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二十年馆长的亚当•韦恩伯格(Adam D. Weinberg)在对新的学术著作的描述中写下了这段话。自去年十月从馆长的职位退休,二十年来他第一次有充足的安静时间,不受繁忙行政事务的纷扰,专注于思考和写作。退休后,韦恩伯格先是受柏林的美国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in Berlin)之邀,担任了一年的驻留学者,在那里访问了大量艺术家的工作室,并开始筹备德国艺术家夏琳•冯•海尔(Charline Von Heyl;b. 1960)明年在雅典Georgie Economou基金会的个展、意大利艺术家伊莎贝拉•杜克洛(Isabella Ducrot;b.1931)2026年在那不勒斯MADRE博物馆的回顾展,同时着手一本关于当代艺术与精神性空间的新书的写作。
过去一年复杂的中东局势所引发的欧美艺术界、特别是艺术机构在展览安排上的巨大分歧与舆论争端,令韦恩伯格对地缘政治持续变化的环境中,博物馆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当代艺术的政治性有了更深的思考。这一年,对他个人而言,也是不寻常的一年,曾经合作过的艺术家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 1938-2024)、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 1936-2024)相继过世,艺术家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基金会创始人之一、利希滕斯坦的遗孀多萝西•利希滕斯坦(Dorothy Lichtenstein; 1939-2024)也于近期去世了。韦恩伯格在退休前负责的最后一个重要项目,在一年内筹款1500万美元,与多萝西及利希滕斯坦基金会合作,将罗伊•利希滕斯坦生前位于纽约西村的工作室改造成惠特尼美术馆著名的独立策展研究项目(The Independent Study Program-ISP)的新的永久性工作空间。
 亚当•韦恩伯格(Adam D. Weinberg) 在艺术家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的工作室,其身后为利希滕斯坦的作品Garden Brushstroke (1996/2009),摄影:Filip Wolak
亚当•韦恩伯格(Adam D. Weinberg) 在艺术家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的工作室,其身后为利希滕斯坦的作品Garden Brushstroke (1996/2009),摄影:Filip Wolak 回顾自己在欧美不同博物馆工作了四十五年的职业生涯,韦恩伯格很欣慰,终于告别了那种以小时为单位划分工作时间、被无尽工作会议占满的管理者身份,回归到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上:与艺术家们工作、策展、思考、写作。
今年夏天,韦恩伯格从欧洲回到缅因州的家里,远离纽约市的喧闹,专注于策展的筹备和新书的创作。
delvsie.com谈艺录与韦恩伯格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前的一次谈话完成于他去年春天即将退休之前。此文的对话部分将两次谈话的内容综合而成,韦恩伯格回顾了他在惠特尼前后工作三十年(包括担任馆长二十年)的经历,他为美术馆所带来的改变,当今的地缘政治局势中博物馆的身份与角色、以及为什么他认为所有伟大的艺术都是政治的。
亚当•韦恩伯格于2003至2023年间担任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the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的馆长。他拥有布兰迪斯大学学士学位和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视觉研究硕士学位。韦恩伯格曾担任艾迪生美国艺术画廊馆长、惠特尼美术馆永久馆藏高级策展人、巴黎美国中心艺术和项目总监、沃克艺术中心的教育总监和助理策展人。他曾策划了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理查德•普塞特-达特(Richard Pousette-Dart)、野口勇(Isamu Noguchi)、亚历克斯•卡茨(Alex Katz)、罗伯特•曼戈尔德(Robert Mangold)、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和弗兰克•斯特拉等艺术家的个展。韦恩伯格曾与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小野洋子(Yoko Ono)、白南准(Nam June Paik)、洛娜•辛普森(Lorna Simpson)和杰西卡•斯托克霍尔德(Jessica Stockholder)等艺术家组织过公共艺术项目。
韦恩伯格是罗马美国学院、泰拉美国艺术基金会、Storm King艺术中心和希望之星(艺术家罗伯特•印第安纳(Robert Indiana))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并曾担任美国艺术联合会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视觉艺术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他是美国艺术档案馆咨询委员会、伊斯坦布尔Sebançi 博物馆科学委员会和多哈Art Mill博物馆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以及那不勒斯 MADRE 博物馆馆长选拔委员会的成员。他曾担任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参观委员会主席、麦迪逊广场公园保护协会艺术委员会成员以及波洛克-克拉斯纳(Pollock-Krasner)基金会评选委员会成员。
韦恩伯格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曾获得美国建筑师协会颁发的功绩奖、纽约大学颁发的纽约市模范服务鲁丁奖、以及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颁发的杰出艺术服务奖。2015年,韦恩伯格被法国政府授予艺术与文学军官勋章。
对话亚当•韦恩伯格
吴可佳:您在惠特尼美术馆前后工作逾三十年,在此期间美术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馆之一。公众对于惠特尼双年展比较熟悉,但对于惠特尼美术馆创立的历史可能所知不多。您能跟我们回顾一下美术馆的历史吗?
亚当•韦恩伯格: 惠特尼美术馆创立于1930年,创始人是格特鲁德•范德比尔特•惠特尼(Gertrude Vanderbilt Whitney;1875-1942)。
她出生于当时美国最富有的家庭之一,但她的婚姻很不如意,后来开始学习艺术创作,与此同时,她希望在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之外,开辟一处精神追求的空间。在创作艺术的过程中,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这都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事情,那时美国并没有真正本土的当代艺术家社区,美国艺术家的群体很小,艺术市场对美国艺术的需求也很少。在19世纪,美国艺术家的创作,主要还是以欧洲艺术的发展为坐标,他们或者到欧洲接受艺术创作的训练,或者通过研究欧洲艺术来启发自身的创作,很少思考美国的艺术发展可能是怎样的。
 Gertrude Vanderbilt Whitney肖像(1916),艺术家:Robert Henri,布面油画, 126.8×182.9厘米,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New York;由Flora Whitney Miller捐赠 86.70.3
Gertrude Vanderbilt Whitney肖像(1916),艺术家:Robert Henri,布面油画, 126.8×182.9厘米,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New York;由Flora Whitney Miller捐赠 86.70.3 因此那时是以惠特尼女士为主,开始发展这样的想法:鼓励真正富有美国特色的美国艺术的发展。她成了那些在美国工作、生活的艺术家的重要推动者。在惠特尼生前位于曼哈顿下城的工作室,她经常举办各种艺术展览、讨论艺术的沙龙活动等。1930年,她决定创立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以鼓励生活在美国的艺术家,令他们有一个展示作品的空间,因为当时美国主要的美术馆,例如大都会博物馆,都不展呈美国艺术家的创作。实际上,1929年惠特尼曾向大都会博物馆提出,捐赠她个人收藏的美国艺术家的作品,并同时捐赠一百万美元,而大都会博物馆拒绝了她的捐赠---当时大都会博物馆认为这些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不好”。这是她决定建立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的主要动因。
今天,惠特尼美术馆的重点是鼓励与支持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现世艺术家的创作。理解我们的工作角色的最好角度是:我们是艺术家的美术馆,艺术家的创作关注在哪些领域,我们的工作重点就在这些领域。这是惠特尼美术馆的历史背景,再过几年,它就有一百年历史了。
我首次到惠特尼美术馆工作是1989年,先后三次进入惠特尼美术馆工作,工作的性质都不同。第一次是80年代在惠特尼的一个分馆担任策展人,负责那所分馆的馆藏。当时那个分馆位于曼哈顿57街与第七大道的一座大型办公楼的两层,有两间展厅,每间大约1500平尺,其中一座展厅展示惠特尼的永久收藏,另一座展厅举办特展。我在那里担任了三年的策展人,之后到巴黎的美国中心工作(注: 担任艺术与项目总监)。
90年代,我从巴黎回到纽约,负责惠特尼美术馆的馆藏,工作六年之后,我到马赛诸塞州的艾迪逊美国美术馆(Addison Gallery of American Art)担任馆长。2003年,我再次回到惠特尼美术馆,担任馆长,所以惠特尼馆长的工作做了二十年,与惠特尼美术馆前后的工作关系,差不多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我曾经与之前的三任馆长共事,既受到他们工作的启发,也对美术馆的管理有不同的想法。
吴可佳:如果您回顾几十年前开始在惠特尼工作那段经历,当时的美术馆是怎样的状况?
亚当•韦恩伯格: 惠特尼美术馆之前所在的布劳耶大楼(Breuer Building)是1966年落成的。这栋楼由建筑师马歇•布劳耶(Marcel Breuer)设计,位于曼哈顿的上东区。那时惠特尼的馆藏大约有6,000件作品,现在的馆藏大约为27,000件作品。我们从曼哈顿上东区搬到下城的原因之一是布劳耶大楼的空间不够,而馆藏已经是之前的逾四倍。不仅如此,当代艺术作品的体积比过去大多了,过去馆藏的艺术品多为架上作品,后来馆藏纳入了像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创作的大尺幅的作品、以及其他艺术家的装置作品,有些单件作品的展呈能占据一个房间,或者是影像作品的展出,投影成像的呈现等等,都需要更大的空间。
布劳耶大楼是一栋优美的现代建筑,但随着惠特尼馆藏的扩大,不仅是展示作品的空间不够,这栋楼也有自身的问题,它像一个城堡,窗户不多,室内的视觉体验不够明亮,从观者的体验而言,过于严峻,不容易接近,缺乏参观的吸引力。对于那些从未或很少去美术馆参观的公众而言,他们可能没有兴趣走入这栋楼。
当我们计划搬到曼哈顿下城之后,为我们所聘用的设计惠特尼新馆的建筑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提到的设计要求之一,是我们希望新馆是一座更具开放性、更有包容性的建筑。他设计的这栋新楼,建筑富有透明感,公众很容易在展厅感受建筑户外的景观。这种透明感不仅是公众在建筑中所体验的户外风景---我称其为360°美术馆,从这栋楼,你能以360°看到纽约市的风景,你既对自己所处的空间有一种现场感,而从周边的建筑、如麦迪逊大街的楼里,也能看到你---更重要的是,这栋楼能让参访者们感到充足的光线所带来的轻盈感、透明感、包容感,而不是那种走入美术馆后,不知自己将获得什么的感受。
布劳耶大楼给公众的感受是,“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想走入,因为我不懂现代艺术”,会令公众感觉紧张。
 1970年代的布劳耶大楼(Breuer Building),惠特尼美术馆旧址。摄影:Jeff Goldberg/Esto
1970年代的布劳耶大楼(Breuer Building),惠特尼美术馆旧址。摄影:Jeff Goldberg/Esto 而新的惠特尼美术馆,在建筑前端的户外有艺术品、楼上的露台有雕塑、当进入此建筑,你立即就知道该去哪里参观。搬入曼哈顿下城的新馆后,我们的访客量很快就翻了三倍,从平均每年40万到逾120万。这不仅是因为建筑的体量变大了,主要是新馆的空间更富有亲和力。
之前在纽约上东区,惠特尼美术馆的存在处于其他大美术馆的阴影之下,如全球最好的一批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古根海姆美术馆,其建筑本身充满了吸引力,布劳耶大楼相形之下,像个黑箱子。古根海姆美术馆虽然没有什么窗户,但这座螺旋上升的建筑体,让公众有强烈的欲望进入其中体验艺术。而距离不远是纽约现代美术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MoMA)。相比之下,那时的惠特尼美术馆像个纽约艺术界过继的孩子。
当惠特尼搬到曼哈顿下城,我们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身份与自由,像一个孩子必须得从家里搬出来才能获得独立,成为她自己。我觉得,惠特尼从纽约上东区的青少年时期,过渡到纽约下城的成年时期---拥有充足的建筑体量、空间感,与建筑前的哈德逊河发生联系。1930年惠特尼美术馆刚成立的时候,就位于纽约下城,距离现在的新馆十个街区。纽约的下城一向是当代艺术家们生活与艺术创作活跃的地区,而不是上城。因此我们回到了艺术家们的社区,回到了我们最早创立的地区。伦佐•皮亚诺曾经说,当你们(惠特尼)在纽约上城的时候,你们是拥有下城的(艺术家)精神的上城美术馆。现在我们回到了真正属于这种精神的社区。
 惠特尼美术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的新馆建筑。摄影:Ben Gancsos
惠特尼美术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的新馆建筑。摄影:Ben Gancsos 吴可佳:如果咱们聊聊您二十年前担任馆长初期,那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除了美术馆建筑本身的挑战之外?
亚当•韦恩伯格: 建筑的楼体本身是很大的挑战,惠特尼的馆藏增长了很多(二十年前已经有两万多件作品),因此我们总是面临这样的两难局面:是该多展示美术馆的永久馆藏,还是该做更多的特展?做特展的优势是,能够呈现当代艺术界最新的动向,但挑战在于如果公众希望看到更多的永久馆藏,展厅的面积就不够了。
在惠特尼的新址,我们能更好地保持二者的平衡,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此外布劳耶大楼的建筑布局没有公教空间、没有剧场,除了地下一层的餐厅,并没有一个专门令公众聚集的空间。由于建筑空间有限,当时美术馆大部分工作人员的办公室都不在布劳耶大楼,包括我自己的办公室,我那时的办公室在旁边一栋建筑的楼里,其他美术馆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分布在纽约不同区域的办公楼里。我觉得对于辅助性部门如财务部等,这样影响不大,但对于策展部、公关部、公教部的工作人员,最好应在艺术品展厅所在的建筑里办公,否则就很难建立一个真正的艺术社区。
因此当时另外一个挑战是,很难在美术馆的工作人员中建立一种社区感。我被任命为馆长时,美术馆的员工们与董事会的想法很不一致,员工之间也对美术馆所代表的艺术身份有相互疏离的观点---有些员工认为惠特尼代表了当代艺术,另一些员工则对历史性艺术感兴趣,导致当时的机构身份像一个楼里的好几座美术馆。所以我着手处理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以一个共同的目标,将员工们凝聚在一起。 (注: 当时美术馆有200名员工,每年的运营经费为2000万美元,现在逾400名员工,每年的运营经费为6500万美元; 在韦恩伯格担任馆长期间,美术馆的捐赠基金从初期的4000万美元增长为四亿美元,包括为新楼的筹款工作,韦恩伯格在任期间美术馆筹款金额逾7.65美亿元)。 除了这些数字上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年实现了一种社区精神:包括美术馆与公众之间的社区感、美术馆的员工与董事会之间的社区感。
 惠特尼美术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的新馆建筑。摄影:Nic Lehoux
惠特尼美术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的新馆建筑。摄影:Nic Lehoux 其次是扩大我们之前所定义的“美国艺术”的范畴,例如:纳入那些居住在海外的美国艺术家的创作,以及来自海外、在美国生活的艺术家的创作。同时,将来自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艺术家包括进来,更多地关注不同肤色的艺术家的创作、原住民艺术家的创作、拉美艺术家的创作。作为美国艺术博物馆,我们需要呈现美国艺术的多元性,这样不同背景的公众来到这里,都能感同身受。在那时,若你是亚裔的访客---在美国最大的三个亚裔群体---华裔、日裔、韩裔---到这里却很难看到一件亚裔艺术家的作品。我们当时虽做过重要的野口勇展览,但这样的展览极少。对于拉美裔艺术家的作品呈现也是类似的状况,而纽约市30%的市民都是讲西班牙语的。虽然不是说,我们必须按照这样的比例策划艺术展,但那时的展览缺乏多元性的状况是不对的。
现在惠特尼展呈的艺术作品的多元性要丰富得多。我们是美国第一家举办草间弥生回顾展的美术馆,从50年代她住在纽约的时候就开始收藏她的作品。现在大家都知道她,但我们已经收藏她的创作逾60年了。白南准在美国的首次回顾展也是惠特尼美术馆策划的,我们是最早在学术界推广他的创作的机构,每次我去韩国出差,他们都会提到这一点。
吴可佳:当时您面临这些挑战的时候,是如何进行战略规划,令惠特尼实现一系列转变呢?
亚当•韦恩伯格: 我们制定了好几个战略规划,其中一个的核心是专注于需要建一座新馆的诉求,这个规划大约在十年之前,主要讨论为什么我们需要一座新馆、这座新馆将为我们带来什么?
如格特鲁德•惠特尼的孙女对我所言,惠特尼美术馆不是一栋楼,而是一个(关于艺术的)思想。这句话很重要---这座美术馆的目标一向不是一栋大楼,美术馆的建筑仅仅是思想的载体、艺术品的载体、与公众交流的载体、艺术项目的载体。一栋好的建筑能有效地为这些目标服务。
吴可佳:事实上亚洲地区的很多美术馆是相反的思路,结果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同的挑战。
亚当•韦恩伯格: 的确如此,很多美术馆是先建一栋楼,认为楼建好了就实现了工作目标,但如果你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就像你对自己的情况不了解,怎么去购置服装呢?如果你是爱好运动的人,买的衣服就和商务人士是不同的。衣服是代表你的,也是你的建筑。每个人的着装都反映了他们是谁、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事情、他们的想法、他们的优先事项是什么,而这就是建筑必须做的事情,它们必须对优先事项做出反应。
吴可佳:回到您提到的战略规划,我猜想您当时做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与员工们、与董事会讨论,惠特尼美术馆所代表的艺术思想是什么?
亚当•韦恩伯格: 是的,当时的想法是要建立一个艺术社区,充分认识到与五十年前相比,当代艺术已经非常不同了,美术馆需要更为敏感地对艺术和艺术家做出反应;美术馆应是令人们能够参与进来的艺术社区,以及能让残疾人容易进入欣赏艺术的建筑体。同时重新定义“美国艺术馆”----到底什么是美国艺术。
过去很多年,许多人都以为能够定义美国艺术。这个挑战我称之为“美国艺术的洋蓟哲学”(artichoke philosophy of American art)---过去多年间,很多人认为如果你不停地把叶子剥掉,就能接触到核心。因此几十年期间,人们试图定义”美国思想“的核心是什么。但实际上这是不存在的。这些叶子才是核心,而不是人们所认为的这个内核---每一片叶子都代表了这个文化的一个部分,它的历史、想法、概念,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试图呈现这个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这种多元化与复杂性才是最精彩的。当然推动这些多元层面的后面有一个民主的思想,民主是关于人的,而不同的人(公众)有那么多,你怎样才能让这些不同的人都(在美术馆的艺术中)感到一种认同感? 赋予人们发声的机会,这才是民主最根本的方面。
因此,包容性、开放性、可访问性、民主、追随艺术家的理念,这些都是我们的创始理念,新馆的建立是对于这些理念的重新诠释。
按照这些思路,我们对惠特尼新馆的建筑有了明确的想法。从2017到2022年,我们又制定了新的战略规划,包括更多地纳入原住民艺术、拉美艺术等,美术馆的关注集中于我所谈到的三个A: art(艺术)、artists(艺术家)、audiences(公众)。
 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个展“Edward Hopper’s New York”现场,(2022年10月-2023年3月),摄影:Ron Amstutz
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个展“Edward Hopper’s New York”现场,(2022年10月-2023年3月),摄影:Ron Amstutz 吴可佳:谈到惠特尼对于馆藏与展览的安排,馆内既有像爱德华•霍珀这样美国历史上重要的画家、又有像郑曦然(Ian Cheng)这样新一代数字艺术家,如何在策展部保持智力探索的平衡呢?
亚当•韦恩伯格: 首先,不像很多其他美术馆的策展人,只专注于一个领域的策展与研究---如策展人仅专注于一个文化历史阶段、或者一类艺术创作媒介(如摄影),惠特尼美术馆的策展人---如我们负责摄影策展的策展人还策划过很多绘画与雕塑展、策划过两届惠特尼双年展,我们的素描与版画策展人刚策划了一个重要的爱德华•霍珀绘画个展,因此,在某个领域有特别学术专长的策展人,在惠特尼不是仅策划她(他)这个领域的展览。而像大都会博物馆这样的机构,如果你是摄影部的策展人,就不会负责油画展、版画展的策展、或者亚洲艺术部的策展。在惠特尼,如果策展人的专长是20世纪初的艺术,你还是有机会做当代艺术的策展。例如惠特尼刚举办的目前住在洛杉矶、当代非裔艺术家亨利•泰勒(Henry Taylor)绘画展的策展人芭芭拉•哈斯凯尔(Barbara Haskell),她之前所专注的学术领域主要是二战前的当代艺术。
我们看重的,是每位策展人在20和21世纪美国艺术的任何领域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想法提出策展方案的能力。我们从不试图把艺术局限在一个狭隘的盒子里,跟策展人说:你必须仅专注于20年代的艺术、或者雕塑这样的艺术形态。策展人有能力策划不同领域的展览是很好的事,这是很大的自由,而艺术家们所寻求的就是自由。
吴可佳:我在几年前与大都会博物馆馆长麦克斯•霍伦(Max Hollein)讨论这个话题,他谈到大都会博物馆试图打破部门的界限进行展览的策划,但这很难。
亚当•韦恩伯格: 是的,对大都会博物馆而言,这样的尝试太难了,因为他们的馆藏跨越了数千年的艺术,而我们馆藏艺术品的历史跨度只有一百多年。
同样纽约现代美术馆的馆长格伦•洛瑞(Glenn Lowry)也曾希望做这样的尝试,合并一些部门、拓展更开放的策展领域,但对MoMA而言太困难了,他们馆藏与策展是严格按照艺术门类来组织的,例如版画、摄影、表演艺术等,因此他们只能按照这样的格局来工作。而大都会博物馆的专业细分更为严格,也只能这样延续下去。我们在策展领域的灵活性,从某些角度而言甚至超过了纽约的新美术馆(New Museum),因为新美术馆虽然是当代艺术馆,但他们展览所包含的艺术家更为国际化(需要了解不同地域文化的策展人)。
吴可佳:所以这些打破策展部门界限的改革,也是您担任馆长后所带来的变化之一?
亚当•韦恩伯格: 是的,其实在60-70年代,我们的策展部没有那么多界限。我的前任馆长给策展团队设置了很多部门,他按照艺术史发展的思路进行了门类细分。我上任之后感觉这样不合适,这种门类细分不是惠特尼美术馆的优势,因为我觉得惠特尼的艺术不是关于分门别类,恰恰相反。
所以我取消了这样的门类划分,并进一步强调美术馆各艺术领域之间的关联。当我每次选择策展人加入惠特尼的时候,他们的头衔都是这样写的:”策展人/摄影策展人”、”策展人/版画策展人”,我想强调他们首先是策展人,其后再谈到他们的学术专业。我们没有策展的部门细分,如版画部、摄影部等。有首席策展人(chief curator)负责策展部门,整个团队一起工作,提出策展方案。而且大家都很清楚,即使是具有摄影学术专长的策展人,也可能策划雕塑或装置展。
吴可佳:疫情期间我和作曲家史蒂夫•莱奇(Steve Reich)有一次谈话,他对于1969年参加的惠特尼群展仍记忆犹新,说那次展览包括许多不同创作媒介的艺术家的作品,包括迈克尔•斯诺(Michael Snow)、理查德•塞拉等,他们都很喜欢当时展览所呈现的活力。
亚当•韦恩伯格: 的确如此,这是惠特尼美术馆的精神根源。惠特尼历史上一直都有表演艺术项目,后来由于建筑体的空间不够,很多表演艺术活动不得不挪到分馆的建筑。我担任馆长后,说表演艺术非常重要,为什么不策划更多的表演艺术项目呢?随后我们有了第一个表演艺术的策展人利莫尔•托莫(Limor Tomer),她后来加入大都会博物馆,负责那里的表演艺术项目。现在的表演艺术策展人阿德里安•爱德华兹(Adrienne Edwards)策划了爵士音乐家杰森•莫兰(Jason Moran)在惠特尼的个展,还策划过惠特尼双年展、以及不包括表演艺术的展览。
我在任期间感到最自豪的一项工作就是把表演艺术放到惠特尼美术馆的重心,并与其他的艺术形态进一步地整合。
吴可佳:近年来惠特尼美术馆对富有争议的艺术事件的处理,也体现了对艺术家的尊重,这一点在纽约市都是难得的范例,例如2017年惠特尼双年展对艺术家戴纳•舒茨(Dana Schutz)绘画示威事件的处理。
(注:2017年的惠特尼双年展展出了戴纳•舒茨2016年的油画作品“打开的棺材”(Open Casket),画面基于1955年14岁的非裔美国男孩埃米特•提尔(Emmett Till)被诬陷与一位白人女性调情而在密西西比州惨遭杀害,提尔的母亲坚持在葬礼上打开棺木,让人们看到埃米特所遭受的残忍私刑。2017年舒茨的油画在惠特尼展出时,纽约一批非裔民众批评舒茨作为白人艺术家创作此题材,强烈要求惠特尼美术馆撤出此作,美术馆未同意。在双年展期间的示威过程中,一些示威人士常以身体将画作包围起来,令其他参访者看不到作品,直到当日美术馆下班)
亚当•韦恩伯格: 是的,当时是一个相互做出让步的局面,非常困难,但在示威者们进行抗议的过程中,我们组织了讨论的论坛,我们认为,只要大家不去伤害对方、不去毁坏艺术、破坏美术馆的建筑体,我们觉得大家必须相互做出让步。我记得当时美术馆的一位董事会成员说,亚当,你总是说,你希望人们参与对话,但最终是怎样的对话,并非由你来选择。
这也是我所提到的公众永远不只是一种角度的观点,公众有各种角度的意见,不是二元的,而是多层次、复杂的。这就是为什么一座美术馆应该包容不同的观点,你可以有亚裔犹太艺术家约什•克莱恩(Josh Kline)的个展、也有原住民艺术家杰恩•史密斯(Jaune Quick-to-See Smith)个展、黑人艺术家亨利•泰勒的个展、日裔美籍艺术家鲁斯•阿萨瓦(Ruth Asawa)的个展。
我理解一些民众为什么会对戴纳•舒茨创作埃米特•提尔的画面题材感到不满,然而一旦我们把作品挂在墙上,我们就不会对其进行审查,一旦它挂在墙上,它就会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这是作品被展览的原因。
 鲁斯•阿萨瓦(Ruth Asawa)个展“Ruth Asawa Through Line” (2023年9月–2024年1月)现场,摄影:Filip Wolak
鲁斯•阿萨瓦(Ruth Asawa)个展“Ruth Asawa Through Line” (2023年9月–2024年1月)现场,摄影:Filip Wolak 吴可佳:我记得之前与大都会博物馆馆长麦克斯•霍伦的讨论中,他谈到近年来大都会博物馆更多地在重要的国际政治事件上表达机构的立场。在这方面,您在惠特尼美术馆担任馆长期间,是怎样的思路?
亚当•韦恩伯格: 我觉得如果你展示的是当代艺术,那么你所面临的就是世界上所有的(政治)问题。如果你说,“我将处理政治问题”,那么你就把自身放入了一个二元论的领域里---有关于艺术的艺术,此外有关于政治的艺术。而我是不认可这种二元划分的。
我认为美术馆将持续作为社区各个群体交流思想的聚集场所,因此美术馆本身不应公开声明政治立场。我始终相信艺术家们需要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和平台,而美术馆一旦发表政治声明,就很容易陷入派系立场。我觉得美术馆必须成为能赋予(不同观点的)对话的场所,为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思考、创作、存在与行为提供多样化的方式。最近这些年的趋势是,试图将美国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拉入其中,使其成为政治讨论的行动者,而不是圆桌对话场域的提供者。
美术馆应该像一个社交场合或一顿饭的主人,邀请不同观点的人们入席。作为主人,我们有责任为每个人提供在餐桌上发表观点的机会与空间,我们的工作不是发号施令,告诉人们应该怎样,而是将人们聚集在一起,深入倾听他们的观点,然后试图将各种观点与对话综合起来,展示、呈现我们认为很重要、非常有关联的艺术作品与思想----那些能改变人们生活的作品与观点。这才是美术馆的工作,是一个呈现者的角色。对此我深信不疑。
吴可佳:特别是在您去年秋天退休后、到柏林进行学术驻留这段时间,欧美的许多艺术机构由于对中东危机的观点迥异,很多艺术家的展览被取消,这种现象已从视觉艺术领域蔓延到更广的文化机构。
亚当•韦恩伯格: 的确如此。我非常理解现在的这种情况,不是说我不同情其中的许多成因,但我个人的同情不是最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美术馆因艺术家的政治立场而取消其展览)无助于创造一个对话的圆桌场域,因为十年之后,又会出现新的政治问题,甚至十分钟之后,又可能有一个不同的政治问题,一座博物馆是否应该对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表明立场?
我觉得美术馆并非所有政治问题的专家,如果我们对所有人类社会的每个争端都试图做出立场声明,我觉得这不是美术馆的工作。我理解,美术馆是人们的政治立场获得关注的地方,但美术馆本质上关注的是视觉艺术的概念。我觉得直接的政治活动与艺术表达之间,是存在区别的。例如艺术家汉斯•哈克(Hans Haacke)的创作---作为艺术家,哈克本人的政治观点一向极为鲜明,而他艺术作品的视觉呈现却富有复杂的层次。例如他多年前在威尼斯双年展的作品,整个德国馆的地板被打碎,我觉得这件作品是最有力的政治声明之一,但不是非常具体的书面声明。它是一份视觉声明,讨论了人类文明、权力、制度、政治与政府的本质,所有这些元素都包含在作品之中。对我而言,哈克的这件作品比简单的政治口号更有力量。
或者你看艺术家珍妮•霍尔泽(Jenny Holzer)的创作,当她使用文字时,充满了层次感,它们有双重含义、同义反复、复杂、有诗意、既有节奏感、视觉上又有趣,你阅读她的文字,会沉浸其中,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它,她的文字让我们对其既具怀疑,又理解这是艺术家的一种工作方式。她的作品非常政治,而同时又具有开放性。
我觉得那些既政治、又富有开放性、能够提出更多问题的艺术作品,相比仅提出一个政治口号、或者回答某些问题的作品,有力量得多。
吴可佳:今年五月艺术家弗兰克•斯特拉于87岁高龄去世,2015/2016年斯特拉艺术生涯最后一个大型回顾展在惠特尼美术馆举办,您是策展人之一。在与艺术家几十年的友谊之中,您如何看待他的艺术创作精神气质?
亚当•韦恩伯格: 弗兰克是我所认识的最有勇气的艺术家之一。我曾经跟他开玩笑说,”弗兰克,你可以画一辈子黑色的架上系列。”,这也是他最知名的绘画系列。他打趣地回答说:“我希望你早点告诉我。” 我说,弗兰克,我的意思是,你知道自己只需一直画早期风格的架上系列就能维持创作生涯了,但你选择了不停地往前走,甚至常常走在观众的欣赏水平之前、甚至艺术市场对你的创作转变有时毫无反应。你尝试了这么多的系列、这么多不同的媒介、有些时候我对你的新的创作系列也不欣赏,但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有这样的勇气---工作告诉你去哪里、你的想法告诉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从不放弃。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标志,而不是仅满足于自己获得的艺术桂冠。
 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个展“Frank Stella: A Retrospective” 现场(2015年10月—2016年2月),摄影:Ron Amstutz
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个展“Frank Stella: A Retrospective” 现场(2015年10月—2016年2月),摄影:Ron Amstutz 大部分艺术家以十年或者二十年的非常优秀的创作而闻名,而弗兰克的重要创作持续了大约六十年,无论你是否认为他这些年的每件作品都那么精彩。毫无疑问,他是位极具影响力、令人钦佩和尊重的艺术家。
 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个展“Frank Stella: A Retrospective” 现场(2015年10月—2016年2月),摄影:Ron Amstutz
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个展“Frank Stella: A Retrospective” 现场(2015年10月—2016年2月),摄影:Ron Amstutz 弗兰克的一生对艺术最根本的追求是探究绘画的本质是什么、艺术创作的本质是什么?到什么程度,一幅画就变成了别的东西?雕塑在什么时候真正成为一幅画,或者一幅画开始变成雕塑?在某种程度上,他以劳森伯格的方式提出了一些相同的问题:一幅画与墙壁的关系是什么?是什么让绘画成为绘画?这种哲学性的探究。在他创作生涯的早期,他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减而又减的还原方法试图获得绘画的本质;到后来,他往画面中掷入一切,试图找出任何事物的本质。所以他像艺术科学家一样,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来处理这种探究。我认为弗兰克那些最成功的、甚至晚期的一些作品都是那种将极简主义嵌入到一种极盛主义方法中创作的作品。
吴可佳:过去咱们多次的谈话中,您经常讨论到所有伟大的艺术都是政治的,能否就此再聊聊您的想法?
亚当•韦恩伯格: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关于示威(protest)的基于永久馆藏的策展,展览中包括艺术家艾德•莱因哈特(Ad Reinhardt)的作品,他的抽象画作非常有政治性,因为是关于语义的微妙性、对于传统绘画方式的拒绝、同时也是关于一种新的维度。我觉得所有伟大的艺术都是政治的,将艺术划分为直接的政治性和非直接的政治性,实际上对于那些创作政治色彩鲜明、但其表达远远超出政治性的艺术家们,以及那些被人们视为创作不具政治性的艺术家们,都是不公平的。例如(通常被公众认为是极简艺术家的)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他的艺术创作极富政治性,因为他的艺术是关于重新思考空间、时间、艺术创作的未来、关于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里、艺术为我们的对象起到怎样的作用、以及艺术是什么的重新思考,这些提问都是富有政治性的。
归根结底,我觉得那些观点---认为艺术创作没有大写的P(Political),就称其不具政治性是荒谬的。
吴可佳:例如理查德•塞拉和弗兰克•斯特拉的创作,是非常政治的。
亚当•韦恩伯格: 是的,他们的作品非常有政治性。我认为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是政治性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让我们重新思考等级制度,让我们思考谁在顶层,谁不在顶层,以及为什么他们在顶层,并让我们深刻地思考这一点。对我来说,这就是最终的政治。这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具体的(政治)缘由,而是关于我们如何思考,在我们的思想如此受控的文化中,思考自己的想法是一种自由。
我们需要这种自由的能力,需要能够真正跳出常规、跳出思维定势的思考。我认为在艺术领域我们可以做到,而且我指的不仅仅是视觉艺术,包括舞蹈、戏剧、音乐、文学和诗歌,以及其他一切,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拓展思维的方式。
文章编辑: dolighan.com